 2024-11-12 16:22
2024-11-12 16:22
 2490次阅读
2490次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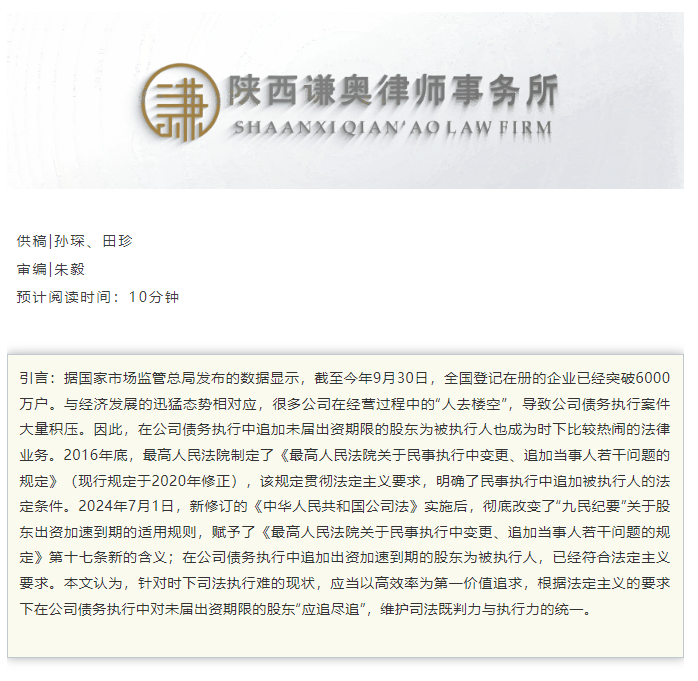
在审执分离原则下,关于在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正当性问题,学术界曾提出“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和“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两种理论予以解释。其中,既判力指的是司法裁判对债权、债务等争议具有的终局确认力,执行力则是指司法对既判力具有的维护和强制力,既判力与执行力密不可分。两种理论均肯定了既判力、执行力指向的权利义务主体应当保持稳定性,同时又肯定了在法定主义的要求下允许权利义务主体扩张至第三人的情形。本文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正实施后(下文统一称为“新公司法”),司法既判力或执行力的扩张应当及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一、新公司法明确规定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情形,填补了立法空白,根本上修改了“九民纪要”的规定 新公司法新增加第五十四条,该条规定了公司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下,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该条法律正式确立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一举廓清了学术界与实务界关于该制度的长期争议。 在该条新规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对如何适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持谨慎态度。2019年出台的“九民纪要”提出一个基本规则,除两类特殊情形外,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新公司法对该规则予以根本性修改,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适用由“原则上否定+个别例外”修改为“原则上适用”。即是说,新公司法实施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适用不仅仅是“九民纪要”规定的“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和“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两种特殊情形,只要公司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一概剥夺,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均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 应当说,新公司法的这一规定针对当下“诚信缺失”“人去楼空”大量存在的现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解决公司债务执行难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上位法依据。 二、公司债务执行中,将被剥夺出资期限利益的股东追加为被执行人符合“法定主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关于“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规定即为通常所说“法定主义”的渊源。 本文认为,上述司法解释第一条所述的“法定条件”不应机械的局限在该司法解释的文义表述中理解,而应当从该司法解释提高债权人利益保护执行效率的立法目的以及上位法体系中寻求“法定条件”的具体适用。其实,综观该司法解释规定的种种“变更、追加”情形,均对应着应上位法依据。即是说,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法定条件”应当以“司法解释+上位法”来统一衡量。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作为被执行人的合伙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普通合伙人为被执行人的,变更、追加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有限合伙人为被执行人在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即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关于“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的“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即对应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2018年公司法规定在第六十三条中)。如此种种,不再列举。但是,如果上位法立法变化赋予了司法解释情形以新的含义,则对此新含义应作为“法定条件”予以肯定,允许既判力或执行力向其扩张。 新公司法未实施前,因为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没有上位法规定,所以在法定主义的要求下,既判力或执行力的扩张并不能当然触及该制度。即是说,没有上位法的支撑,不能直接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在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情形下,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个案中认定认缴制下股东期限利益剥夺的正当性,应当参照“九民纪要”的规定通过诉讼程序加以解决。关于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有相应裁判文书支持。例如:(2023)最高法民申2920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执行程序中追加新的主体为被执行人要遵循法定原则,即追加被执行人必须有法律、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目前并无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可以在股东认缴出资期限尚未届至时,以出资加速到期为由,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因此,无论案涉股东认缴出资期限是否应当加速到期,均不应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 新公司法以新增条文提供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上位法依据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是说,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情形下,股东因期限利益被剥夺应当属于“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情形。因此,允许既判力或执行力的扩张及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符合法定主义的要求,亦与上述司法解释提高债权人利益保护执行效率的立法目的相一致。关于此观点,已有法院在司法实务中采纳。例如:北京西城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在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实施当天公布的一则消息“西城法院审结首例适用新公司法加速到期规则案件”。该案中,西城法院在执行生效调解书确认的某公司拖欠其员工工资过程中,经财产调查未发现公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书。其后,该员工向该院申请追加该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西城法院查明,该股东持股比例60%,认缴出资额180万人民币,认缴出资日期为2052年3月15日,依法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 三、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情形下适用的探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对于该条规定情形的适用具有复杂性,探讨如下。 (一)新公司法新增的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是否动摇了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九条的上位法基础? 新公司法新增了第八十八条第一款,明确了股东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即转让股权情形下,应当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该条规定是否意味着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的“原股东”已经不再作为主要出资义务主体,而仅仅作为“补充责任”主体出现?是否意味着在公司债务执行中,应当以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是否动摇了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九条的上位法基础? 本文认为,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的“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同样被新公司法第五十四条赋予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新含义。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指向的是股东在享有出资期限利益情形下转让股权的出资义务问题,并不指向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情形。因此,新公司法该条规定与司法解释第十九条适用空间不同,并不冲突。 (二)股权转让情形下,既判力或执行力不得扩张至继受股东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既判力或执行力扩张对象仅为原股东,并不包括继受股东。原股东出现的出资加速到期情形,继受股东并不因此而当然被剥夺出资期限利益。基于法定主义要求,在公司债务执行中,不得以原股东被剥夺了出资期限利益为由,直接援引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同时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人民法院案例库编号为“2024-17-5-201-012”的“某勘察公司与某科技公司执行异议案”裁判要旨认为,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中,当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该公司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的原股东及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对于能否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由于涉及实体事实判断与责任承担,不能以执行审查程序直接替代审理程序,即执行程序中不能直接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否则将侵害继受股东诉权,申请执行人可以通过另行诉讼主张权利。 2.在股权发生转让情形下,亦不得直接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将继受股东作为公司股东直接追加为被执行人。有观点认为,继受股东通过股权转让继受了公司股权后,即属于公司股东。对于公司债务的执行来讲,如果出现公司无供可执行财产的情形,即可以根据新公司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将继受股东作为公司股东对待,应当认定其出资加速到期而剥夺期限利益,直接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 本文认为,根据法定主义的要求,此观点并不妥当。原因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股权转让情形属于客观存在,其应当属该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特别情形。根据特别优于一般原则,在发生股权转让的特定情形下,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应当优于第十七条来适用。“2024-17-5-201-012”号入库案例中的争议焦点即为:原始股东和继受股东是否能够同时在执行审查程序中被追加为被执行人。该案中,申请人援引的法律依据包括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和第十九条,人民法院认为两者并不能同时适用,原因即在于此。 四、出于提高债权人利益保护执行效率立法目的,应当降低债权人的诉讼成本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了复议、执行异议之诉等救济途径,对于申请人、被申请人同时适用。在公司债务执行中,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通常发生在对公司终本执行的情形下,以此作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证据。本文认为,由于司法既判力已经确认了债权人的权利地位,基于公平原则不宜再对债权人申请追加被执行人苛以实体法审判的程序负担,而应当确立由被申请追加主体承担司法解释所规定救济程序成本及风险的裁判倾向,此倾向亦与司法解释提高债权人利益保护执行效率的立法目的相一致。上文所述西城人民法院审结的案件中,该院即是在公司债务执行程序中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由股东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最终确认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将债权人的诉讼成本降至最低。 END